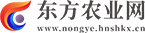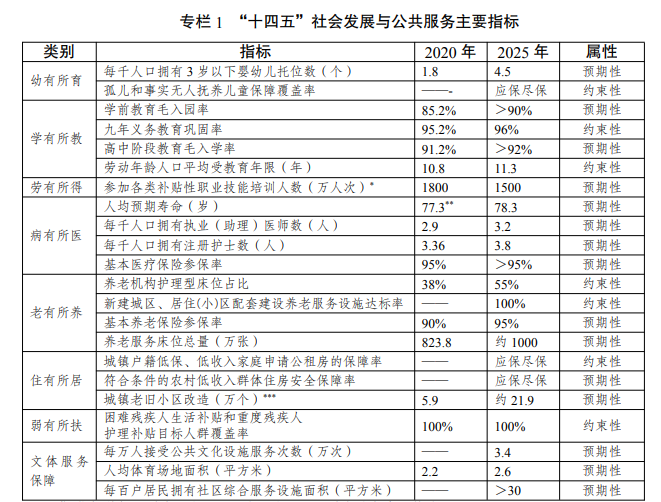B站,我想我,嗯,怎说,我不想说又想说,是呀,好吧。我,算了。我不会说,我那什么,我只想说,一想到你,我就多吃了块红烧肉。你是位美丽的端庄的优雅的摄人心魄的让人入迷的洒脱的飘逸的完美的无缺的神圣的纯洁的不死的不朽的,淑女。哦!我亲爱的淑女,我该如何赞美你而不会遭到你的拒绝。这是个恼人的问题。
 【资料图】
【资料图】
mua,lch liebe dich。
膏沐
话说高木收拾好行李,换了件蓝色圆领袍,缚个牛皮蹀躞,蹬双黑布靴,头裹黑幞头,又系了柄剑,把包袱背了,大步下山,之后便沿着水流走。行过三五天,高木到溪流里洗过澡,没换外套,仅洗了内衣,拿树枝架了放在火堆边烤,再取出面饼来吃。他看过天色,已是正午,有些凉意,又扔些树枝到篝火里。赤霄派素来吃素,戒女色,重孝悌。吃斋守身,故能炼肾精为真炁,而孝悌人伦天生自带,不可去也,亦不可违也。
下午时分,天色晦暗,寒风徐徐,似要下雨。高木将烤干的衣裳叠好收好,踏灭余烬,继续向东北方向前进。至天黑,细雨绵绵。他寻到个山洞,复搭了火堆,趺坐于侧,双臂放两膝,左右手交叠于腹前,闭目入神。没多久,传来阵脚步声,那喘息声也愈来愈近。一位女子闯进洞中,一眼瞧见高木,盯着看。高木睁眼望去,面色平静。外头又来一群人,当头的笑着对那娘子说道:“小娘子,今日你从了我等,好处不尽呐。”女子倒吸口气,猛地转头,要跑,却被抓住头发。当头的狞笑道:“真个香,头发都能掐出水来。”那几个哈哈大笑,旁若无人。高木道:“我拔剑而出,你等必死无疑。”当头的说道:“你是何人?敢扰爷爷的雅兴。”高木道:“粗鄙。”话音尚在,顷刻之间,骨裂声连连。那几个捂着伤处,哀嚎不止。高木道:“速速离去,再逗留,要你等见血。”过不久,其中三人缓过劲来,扶起同伴,纷纷逃走。
女子叉手望地,说道:“多谢郎君相救。”高木拱手道:“扶危救困,乃我赤霄本分。”他收了礼数,又问道:“你这山间的妖精,怎会遇上那帮歹人?”女子仍旧一副矜持模样,说道:“妾是赤狐所化,法力低微,哪打得过那帮土匪?妾从小在这山中修炼,未曾下山半步,也无害人性命,还请道长留得妾一条性命。”“哦?”高木抚过颌下胡须,“看来都是修道之人。我自不伤你,你且去,躲好就是。”女子道:“天黑雨大,衣裳湿透,万望道长收留一夜,让妾烘衣驱寒。”高木道:“你我男女有别,共处一室,恐让他人闲话。”女子哭出一声,啜泣起来,提袖拭泪,说道:“也罢,那些个歹人定不会放过妾,妾这就走。”高木微微皱了眉,说道:“这样,你先把衣裳烘干,我去洞外回避。那些人若乘夜来,定叫他曝尸荒野。”女子擦去鼻涕、眼泪,叉手道:“多谢道长收留,道长恩情,妾万死难报。”高木道:“娘子言重了。”话罢,他走到洞外,立于一丛夹竹桃边。夹竹桃没开花,都是叶子。
山洞里发出的光亮暗了些,没多久又亮了。女子唤道:“道长,进来吧。”高木就进去了,忽闻到一股浓烈而不刺鼻的异香,味道跟檀香差不多,却带丝腥气。他盘腿坐到女子对面,从包袱里拿出个面饼,递过去,说道:“吃吧。”女子道声谢,双手接过,掰着吃。香气越发馥郁,高木只觉得心里有点痒,继续闭目打坐。女子笑了笑,问道:“敢问道长姓名?”高木睁了眸子,说道:“我乃赤霄大弟子,高木。”女子捏下点面饼吃了,含颌笑道:“妾无姓氏,道长可叫妾小狐。”她接着说道:“赤霄派名声早有耳闻,都是行正道,做善事的道士,若有空闲,妾也想去拜访呢。”高木微笑道:“娘子到了山门可报我名号。草木亦可成仙,我赤霄向来欢迎修道者上山修炼。”小狐听了,微微点头,依然不看对方,矜持若处子。她说道:“实不相瞒,我前些日子见了在云霄山的妖族前辈,他说那里云气聚集,天地真炁充沛,比在此处要好上许多。”高木捋了须,开口笑了,说道:“不错,持之以恒,定有所得。你当远离那些入邪的妖怪,秉持正道,这才能喜悦长久,心清神明。”小狐道:“道长点拨,我铭记在心。”高木道:“你先吃,我打坐一会,不怕那几个来。”小狐把面饼放到腿上,叉手道:“道长恩情似海,我无甚银钱,只能感恩戴德。”高木道:“我赤霄救人,无所谓犒赏,为的是道义。”他觉得那香气像水一样,让人有窒息之感,心口似是有根针在扎,又酥又麻。高木挠挠脸,不明所以,接着打坐。
后半夜,小雨,那些人果真回来报复。高木察觉到动静,见小狐睡得熟,就拔出剑,来到洞外。他朗声道:“再不走,叫你等死无葬身之地!”突然,一支箭飞来。高木拨开攻击,立即向箭来处冲去,迅捷如豹。“铮”地一声响,一颗首级跳出灌木丛,继而五六声闷哼。狂风压过树林,微弱火光中,一个人影持剑而立。高木叹道:“唉,杀心不止,如禽兽尔。”他用剑挖出个大坑,将那些土匪掩埋好,念了超度咒语便回山洞了。小狐早醒了,见人进来,纳头要拜。高木扶住,说道:“娘子折煞我也。”小狐坐好,说道:“是我害道长动了杀心,我心有不安。”高木背负双手,说道:“就算佛门也有超度之说,我今日杀了这些土匪,也算是救了今后许多人。娘子自去歇息,待天明再行。”“多谢道长。”小狐含泪点头。高木便去坐着歇息,中间是火堆,对面是躺在地上的小狐。
次日清晨,浓雾弥漫,空气清爽。小狐打着轻鼾,嘴角流着口水。高木收拾行装,踏上路途。他仅仅睡了一个时辰,但他本就精气足,毫无倦意,神采奕奕。山路难行,走得慢,小雨如丝,路泥泞。高木来到溪流边,拿了水袋放到水里去。他扭头去瞧,见个树干边有双亮闪闪的眼睛,跟透明玻璃一样,叫道:“你跟着我做甚?”小狐现出身子,两手握在腹前,眼看地面,说道:“我愿跟随道长,受道长教诲。”高木把水袋口塞上,系在蹀躞上,站起来,一面向对方走,一面说道:“我资历尚浅,你应去赤霄,找我师父周鲜。他道法精湛,能教你许多修炼法门。”话罢,站在小狐面前三尺远处。小狐咬了咬下唇,头埋得更低,小声道:“我只愿服侍道长。”高木道:“我赤霄弟子不能婚嫁,你一个女儿家跟着我,叫他人说闲话。”小狐嗫嚅会,说道:“我也知此道理,可我真的没什么可,可报答的了。”高木笑道:“昔真人西出函谷关,作经书,紫气绵延迄今,也没要报答。我身为道门中人,还求什么酬劳呢?你且去,安心过活,莫要心念此事。行正道便是对我最大的酬谢。”小狐道:“我只想伴道长左右,端茶递水,更衣暖床,都行。”高木抿嘴呼气,说道:“强人所难,未免令人难为。这样,我送你去赤霄,那里多的是瓜木桃李,也有些猎物可吃。”小狐摇摇头,说道:“不去。”高木别过头,长吹口气,说道:“唉,要是让他人知道我与一个女子相伴同游,我赤霄的名声就堕落了。”小狐顿时泪如泉涌,抽泣起来。高木走开些,来回踱步,不时挠挠脖子后面,许久,终于喃喃道:“看来是定有此难了。”他对小狐说道:“你便随我来吧。”小狐用袖子抹抹脸蛋,打着嗝,走到高木身边,伸手去拿他背上的包袱,也不看对方面庞,微笑道:“我,嗝,我来背。”高木道:“跟着吧。”自顾自走了。小狐抿了嘴,又打个嗝,紧跟上。
二人行过三五天,到了定安。此时将近黄昏,高木找到个客栈,租了两间二楼的客房。这小子打开房门,坐到案几边,一眼看见了挂在墙上的女子画像。他羞红了脸,将画像收起,找到掌柜的,换了幅描绘山川河流的水墨画。小狐下来木梯,见高木神色紧张,问道:“道长,怎么了?”高木不接话,快步走进屋里。小狐来到掌柜的面前,又问:“掌柜的,道长怎么了?”这老翁笑道:“没什么。诶,娘子和道长是什么关系?”小狐天真无邪地笑道:“他是我恩人,我是伺候他的。”老翁道:“哦,你们是情侣?怎么住两个房间?”小狐道:“不是,道长于我有救命之恩,所以我就伺候他啦。”老翁道:“原是个雏儿。”“雏儿?”小狐蹙眉,满脸疑惑。老翁清清嗓子,正色道:“你以后就懂了。”小狐眉头更紧,忽舒展开,笑问道:“掌柜的,他刚才找你做什么?是不是吵架了?”“没有。”老翁道,“他找我换幅画。”小狐“噢”一声,指指对方,笑道:“我知道,是那种不穿衣服的画,好不要脸。”言罢,她捂嘴笑起来,往楼上去。老翁不开心了,自言自语:“原是两个雏儿,这玩意多好,唉。”说着,打开账本,拨起了算盘。又听得阵下楼声。那娘子也来换了幅画,换好的恰是齐玲立于河边的人物像。
晚饭时间,小狐端着碗来到高木屋里,坐在他面前,说道:“你都不吃肉,哪有力气?吃点肉吧。”她夹了块红烧肉,要放到高木的碗里。高木连忙避开,说道:“我派吃素,饮食素来清淡。”小狐道:“尝尝么,多好吃。”高木用手盖住碗,说道:“你吃,我吃不来的。”小狐道:“好吧。”把肉塞到嘴里,细细咀嚼。她瞟到山水画,笑道:“这画好,有山有水有人家。”高木问道:“你也懂绘画?”小狐道:“不懂,但我能看出作者的意思。”高木吃块豆腐,说道:“嗯,山水重逢,斜雨归途,思乡情切啊。”小狐笑得缩了脖子,说道:“你才出来几天啊,就想着家了。”高木道:“师父如父,怎能不想?先吃饭。”他大口吃起来。小狐道:“也对,食不语。”她碗里的菜吃光了,要去夹菜。“慢。”高木道,“有肉,不行。”小狐收回手,拿筷子抵住门牙,说道:“我那里都是肉的,我也想吃素。”高木笑了,说道:“吃素必须配合功法,不然肚子疼。”小狐笑道:“道长可以教我呀。”高木道:“我从小习惯了,像你半路去学,很苦哦。”小狐道:“我不怕苦,只要道长教我。”高木道:“行,明天开始教你。”“嗯。”小狐用力点下头,“我能吃了吧。”高木道:“不行,要么换双筷子。”小狐把筷子放到案几上,轻轻嘟着嘴,说道:“一样的呀,我嘴里也有油啊。”高木板起脸,冷眼而对。小狐眼珠子向下转,嘴一皱,小声道:“我,我。”她脸红了,拿起碗筷,快步走向外面。
半夜,雷雨交加,吓得客栈里的牲畜乱叫。小狐惊醒,缩在被子里,不停地发抖,嘴里还不断念着:“不要打我……”忽然,闪电平息,隔了大概半刻钟,又是一声巨响。小狐崩溃尖叫,快速爬到墙角,抱紧膝盖,边哭边战栗着,两眼无神。高木起身穿衣,把灯笼点了拿了,到小狐客房门前敲几下,唤道:“小狐,小狐。”雷声滚滚,风呼啸,哭声凄惨。高木左右看看,见廊道两边都是黑漆漆的,就道:“得罪了。”他一掌拍中门闩部位,待里面的闩断开,推门而入,立即过去问道:“小狐,你怎么了?”小狐脸上全是泪,哭得面红脖子粗。高木放好灯笼,右手作剑指,点在对方眉心,相触的地方冒出白色真炁。没多久,小狐平静下来,扑到高木身上,一把抱住。高木连退几小步,急忙说道:“小狐不可。”他将对方双臂拉开,又撤出好几步。小狐仆在地上,哽咽着。高木叹道:“唉,天道无情。”他上前去,蹲下,把住小狐两肩,扶起对方上身,安慰道:“没事的,打雷而已,吓唬那些坏人罢了。”小狐抽两声,抬手摸了摸脸,悲伤地说道:“我,我怕,我爹爹就是被打死了,他也没做坏事……”高木眨眨眼,看过天花板,盯着小狐的眸子,说道:“这本不是我等能知道的,世事无常。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劝。”说罢,紧接着叹口气。小狐带着哭腔说道:“你陪陪我么。”高木只觉心中热气翻腾,拧着眉头说道:“好。”小狐就倚向对方,环腰抱住。高木跪坐下来,两臂下垂,看着墙。他的呼吸时快时慢,又抬起双臂,顿在半空中,许久,或许有好几年那么长的时间,终于顶不住心中的声音,将小狐搂住了。
这小子一直僵持着动作至天明。
几十缕日光透过窗格,像手指,将那二人握住。小狐头顶一条亮,一条黑,头发边叉出来的一圈发丝轻轻摇曳,如光晕。她贴在高木胸膛上的脸蹭了蹭,忽睁开眼,抬首去瞧,又低了头,用手背擦嘴角的唾液,笑了。高木凝视窗户,神色凝重,眸子里却带点笑意。小狐柔声道:“不累么。”高木赶紧放开对方,要站起来,出不来劲,只能坐着了。小狐笑着看向对方,手遮嘴,微笑道:“你,我,我们算是,算夫妻了吗?”高木道不瞧她,闭紧嘴,咬得腮帮子鼓起来。小狐低头一笑,双手捂脸,说道:“抱了应该就算的。”高木道:“我……”他清清嗓子,说道:“我,我先走了。”话罢,艰难起身,踉踉跄跄地往外走。小狐跟过去,要扶,被挣脱开。她问道:“你不开心吗?”高木进到客房里,闩了门。小狐轻轻敲了几下门,说道:“郎君,你可不能不要我。”脚一跺,低头哭了。没多久,门开,高木已系了剑,背了行李。小狐笑道:“郎君,出发啦?”挽住高木的手臂。高木甩开,不吭声,径直下楼,往街上走。小狐追过去,一副委屈样,跟在对方背后。老翁见状,说道:“果真是露水情缘,哼,瞎搞。”
洛州。铁河陪齐玲到城南寻到宅子,早已是物是人非。齐玲望着街对面的府邸,黯然道:“阿河,我们走吧。”铁河道:“嗯,带你去吃好吃的。”齐玲笑道:“还没到饭点呢。”铁河牵起妻子的手,说道:“吃牛杂去,上回在上阳吃到回好的,不知洛州这里怎么样。”随即迈开步子。齐玲道:“吃这干嘛?水煮羊肉才好得很,走,喝汤。”她轻车熟路,不一会就找到了一家羊肉铺子。这铺子两间店面,一边卖羊肉,一边当饭馆。俩人坐在外头的棚子下。店家问道:“客官吃甚么?”齐玲道:“水煮羊肉两盆,香菜多放,再弄两斤饼来。”店家道:“好嘞。”他离去的时候还小声赞道:“俺洛州娘子就是得劲。”铁河笑道:“娘子也算回乡了。”“可不是么,恁多听多学,不就会了嘛。”齐玲捂嘴笑了,身子往后倾。铁河笑道:“搞什么喽,你听得懂?对了,以后我俩吵架就用家乡话,不伤感情。”齐玲笑骂道:“噢,恁个鳖孙,可憨了。”此话一出,旁边的食客哄笑起来。铁河听不懂,傻笑着挠头。店家婆娘端来面饼到他俩案几上,对众人说道:“这叫一物降一物,别看这郎君个大,哎哟,可俊哩,碰着我洛州娘子,熊样。”齐玲笑道:“可不是么,他呀,憨得很。”那婆娘招呼一声,先进屋了。铁河笑道:“出门在外,留点面子呗。”齐玲道:“要甚么面子?你还打婆娘喽。”铁河抬手摸头,不接话。他俩吃净水煮羊肉和面饼,又吃了几个柿饼,待付账时店家还送了五六片薄荷叶,就各含了片,继续逛街。京城比长宁繁华许多,有些景教僧侣,高鼻深目,穿着圆领袍,买菜绕着肉铺走。还有些佛教僧侣,偏袒,光头,挨家挨户,排队乞食,礼貌谦恭,最后走到棵菩提树下吃了,又将钵洗净,衣裳整理好,把带来的蒲团放在地上坐了,开始诵经。许多行人聚集过去,等待之后的布道。另有些道士,大都是其他门派的,以服饰来看,与常人无异,也就修道之人识得真炁,能分辨出来。那夫妻俩闲来无事,站在围着菩提树的人群后听佛门道理。齐玲对宗教事宜并不感兴趣,捂嘴打着哈欠。她踮起脚,在丈夫耳边小声说道:“犯困,回去吧。”铁河低声道:“正到有趣处,你听,因缘际会,多妙。”齐玲细声细气地说道:“什么因缘,无中生有。”铁河道:“我道门也是无中生有啊,有生于无嘛。”齐玲道:“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怎么会有没有生出有来?难以理解。”铁河道:“你看我俩站着的地方不就是空的嘛,无空,我俩怎么站在这里有呢?”齐玲右边眉毛一挑,说道:“有点意思。但我还是觉得儒生的孝悌仁义要实在点。释、道的无,太缥缈了。”铁河微笑道:“娘子好好色,恶恶臭,我祖师爷所说的道在屎溺,自是不可闻了。”齐玲道:“你才好色,你去屎溺之中吧。”音落,转身离去。铁河追上,抓住妻子腕子,说道:“对,我好色,娘子说的都对。什么无中生有,娘子无中生有的本事可不比先贤差。”齐玲笑出一声,扭头说道:“得亏遇着我,换别的女的,早跑喽。”铁河笑道:“谁叫我娘子聪明伶俐,智慧绝伦,那真是……”“这马屁拍的。”齐玲努一下嘴,右眼一眨,“你修你的道,别跟我讲,烦。”铁河牵着妻子走,说道:“以后我俩不讲这个。”齐玲道:“嗯,什么时候回家呀?我想回家了。”铁河道:“明天吧,明师兄还请我俩去伏牛山做客,去吗?”齐玲道:“你去哪我去哪。”铁河道:“也不远,就在雷泽东边两百里外,就当春游啦。”齐玲捂嘴笑道:“风乎舞雩,妙哉。”铁河笑道:“是啊,夫子也是个潇洒的人。”齐玲问道:“那里真的有舞雩台吗?”铁河道:“我也是听说啊,没去过。”“嗯。”齐玲道,“到时可以吃好多好吃的。”“大饼卷葱!”铁河吼一声,带着妻子奔跑起来,穿行于人群中。
他俩出了洛州城,来到洛水边并肩站着。齐玲注视水面,赞道:“这水多清。”铁河笑道:“去洗澡,我给你驱散闲杂人员。”齐玲瞪了丈夫一眼,拍了对方的胳膊,说道:“洛神在里面,羞不羞。”铁河道:“你女子怕什么?”突然,他叫一声,咬住牙齿,右手握住左腕,额头渗出一层汗。齐玲见此,笑道:“人可是包栖氏之女,你言语无礼,烈山氏可看不过。”铁河擦了汗,左手攥了攥,说道:“想必是洛神与此烈山氏真炁有共鸣。”齐玲道:“要你乱说话。”铁河道:“好多了,是我轻佻。”忽然,传来声巨响,敲得人脑仁发颤。他俩转身望去,只见洛州城北的邙山炸开,木石腾空,烟尘冲天而起,其中偶现白色鳞片,可听到响亮的“嘶嘶”声。那尘土散去,一条白色巨蛇赫然现身,高几十仞,长不可测,约三百余丈还不见其尾。铁河道:“好大。”齐玲道:“比刑天还大。”铁河道:“估计这蛇能盘绕城池好几圈。”齐玲道:“走,去高处瞧瞧。”她催动真炁,跃起百丈,浮于半空。铁河紧随而至。齐玲向事发地打量一会,说道:“亲娘嘞,千丈吗?”铁河道:“按书上记载,应龙也没这么大。”齐玲道:“可应龙有神力,与体型无关。”铁河道:“它坐什么呢?莫非是挖洞到这,把山拱开了。”齐玲问道:“过去看吗?”铁河道:“保持距离,看它所为何事。”齐玲点了头,化为红光,飞向白蛇。铁河则变成个电球,跟在后头。城中的修道者们看到天上两个光点正往北方,也都立即飞奔过去。
铁河和齐玲停在白蛇身躯上方百尺,静观其变。白蛇面对黄河,张开巨大的嘴,口中的气管往外喷着白雾。齐玲闻到气味,蹙了眉,说道:“竟然像是早晨雾气般的味道。”铁河道:“它应该是吸取天地真炁为食,若吃飞禽走兽,定不会有此形态。”齐玲笼袖,说道:“它到底要做甚么?全吹到了河上。”铁河道:“不知。”他俩便看着。过了会,一道金光疾驰向那夫妻俩,顿在铁河身边。铁河转头瞧去,见是个相貌威武,四肢粗壮的年轻和尚。和尚合十道:“阿弥陀佛,贫僧自六合寺来,法名悟忍。”铁河面向对方,拱手道:“我乃南阳派铁河。这是我妻,赤霄派关门弟子,齐玲,道号光尘居士。”悟忍道:“二位大名,早有耳闻,今日有缘相见,善哉。”齐玲向悟忍行个叉手礼:“和尚慈悲。”铁河道:“六合寺普度众生,摆渡世人,我心中也敬佩不已。”悟忍笑道:“道长过誉了。我见此巨蛇像是要引水灌城,欲念经感化之。”铁河道:“我俩也不知其真意。若真如师傅所言,我俩愿意帮忙。”悟忍道:“我且试试看,渡不了,还请道长与居士相助。”铁河拍了胸脯,笑道:“定守此诺言。”“我先去了。”悟忍合十欠身,再俯冲至距白蛇左眼几十尺外的半空中,趺坐好,又合十闭眼,念起咒语。梵音阵阵,合于音律,起伏有序,且每句末尾都压着韵。从远处看去,悟忍身躯泛出淡淡的金光,如日头边的亮星。齐玲忍不住夸赞道:“只听其音,已是有道的和尚了。”铁河道:“虽说佛、道有别,念出这样的咒语,也不是一般了。”俩人略紧的身躯松弛下来,都微笑着望着悟忍。白蛇停止喷气,曲头看向那个和尚,瞳孔收缩,不住地吐着大信子。悟忍的声调很稳,丝毫不动。铁河和齐玲出门时没带刀剑,齐玲道:“我去拿。”话落,瞬间消失,又于刹那间现身。她把长刀交给丈夫,又拔出解牛剑,背了牛皮鞘。铁河掣来刀,背了木鞘。他说道:“我俩去给悟忍和尚护法。”随即飞至悟忍左前方,而齐玲在悟忍右前方。铁河拍拍脑袋,说道:“哈,早该护法的,还让师傅等这么久。”他对妻子说道:“但凡白蛇异动,我击其首,你斩其腹部。”齐玲道:“好。”
戛然而止,下回分解。
虎贲2023.3.28